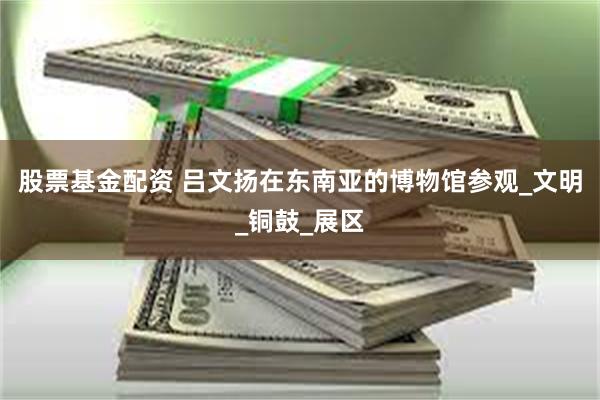
亚热带的午后,雨丝斜斜掠过博物馆的雕花窗棂,吕文扬站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的长廊里,指尖轻触展柜上凝结的水汽。这座博览东南亚文明的场馆,像一艘停泊在狮城的古船股票基金配资,舱内满载着吴哥的砂岩、马六甲的瓷器、湄公河的铜器,正待向参观者展开亚洲东南部的文明长卷。
他的目光首先被一尊吴哥王朝的象神雕像吸引。砂岩雕琢的伽内什神盘坐于莲花座,断鼻处的修补痕迹带着岁月的温度,耳坠的曲线竟与印度卡朱拉霍神庙的石雕如出一辙。底座的高棉文与梵文交错,吕文扬忽然想起课本里的记载:公元9世纪,阇耶跋摩二世将印度教引入柬埔寨,让恒河的神话在湄公河畔长出了吴哥窟的尖顶。
转身进入马来西亚展区,一件16世纪的“娘惹”珠绣褂子泛着珍珠光泽。缎面上,中国的凤凰与马来的木槿用珊瑚珠绣在一起,盘扣的样式是岭南的“蝴蝶扣”,却缀着伊斯兰风格的银流苏。展柜旁的视频里,槟城的娘惹婆婆正教孙女刺绣,口中念叨的口诀竟带着闽南腔:“珠要密,线要直,才像泉州阿嬷绣的样子。”
展开剩余61%越南展区的“黎朝”青花瓷让他驻足良久。一只青花鱼藻纹碗的釉色泛着青灰,鱼的姿态灵动如游水,与他在景德镇古窑见到的明代民窑风格极像,却在碗底多了个梵文“吉祥”印。“越南工匠学了中国的青花技法,却用梵文做款识,专供东南亚的华人寺庙。”导览员递来放大镜,“你看这鱼鳍的笔触,还带着景德镇师傅的影子。”
老挝展区的铜鼓让他想起家乡的苗族村寨。鼓面的太阳纹与广西融水出土的铜鼓几乎一致,只是边缘的蛙饰更显瘦劲。旁边的迁徙路线图上,红线从贵州苗岭延伸至老挝丰沙里,标注着“18世纪苗民西迁”的字样。吕文扬忽然明白,山脉与河流从不是文明的屏障,而是让技艺与信仰流动的脉络。
最让他心头震颤的是印尼展区的“婆罗浮屠”佛塔模型。数百座微型佛龛按层级排列,每一尊小佛像的手势都不同,而塔基的浮雕里,竟有中国唐代的商旅队伍——牵着骆驼的胡人、挑着丝绸的汉人,正沿着山路走向佛塔。“9世纪的爪哇,是佛教徒的朝圣中心,从长安到印度的僧人,都会绕路来这里礼佛。”研究员指着浮雕说,“你看这骆驼的铃铛,和西安出土的唐三彩骆驼铃铛纹饰一样。”
闭馆的钟声响起时,雨已经停了。吕文扬站在博物馆的露台上,看夕阳为展品镀上金边,吴哥的砂岩与婆罗浮屠的模型在光影里连成一片,像极了东南亚文明的版图。他忽然懂得,这座博物馆的“博”,是让山海相隔的文明在此握手;而东南亚的“亚”,从来都是亚洲文明星空中,一颗闪耀着海洋与陆地双重光芒的星辰。
走出馆门,小贩推着沙爹车走过,炭火的香气混着雨水的清新扑面而来。吕文扬买了几串,入口的瞬间,花生酱的浓郁让他想起闽南的沙茶酱——原来味觉早已跨越国境股票基金配资,在唇齿间完成了文明的对话。他掏出手机,给广西的表哥发去铜鼓的照片:“你看,咱们苗家的铜鼓,在老挝也有亲戚呢。”
发布于:天津市